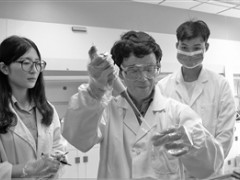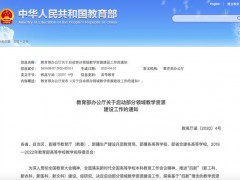在近日“我是科學家”活動現場,生物化學家王志珍與聽眾分享了一個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科研幕后——半個世紀以前,中國科學家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中的創舉,他們的研究已然接近于破譯出蛋白質的折疊密碼,認識到天然胰島素分子是藏在胺基酸序列當中最穩定的結構,但由于任務導向和社會運動的干擾,走到這扇窗戶跟前,卻沒能打開這扇窗。而同期的外國科學家,則在興趣導向的研究中一路探尋,最終捅破了這層窗戶紙,以其科研成果摘得諾貝爾獎。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直到改革開放后“科學的春天來了”,才得以重新啟動,王志珍院士也是在這個時候正式加入的。
我主要講的是中國人當時的精神,這個精神最重要。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原創的問題。只不過中國人沒捅破窗戶紙,是不是?再堅持一下就一定能得到諾獎。”
王志珍院士接受科學大師采訪時這樣解釋她為什么會講這樣一個故事。
當天出場演講的嘉賓中,有三位女科學家,比例很高。王志珍演講完后,問主持人,以往的活動邀請女科學家的比例有多高。得到答案后,她對現場的聽眾說,希望在座的女性朋友都能學習科學知識,“如果能成為科學家、優秀科學家的話,就更好了。”
77歲的王志珍,就身份而論,很為出眾,她不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此前還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不可謂不成功。不過接觸下來,很難將她與副國級領導聯系到一起,平實、質樸,是屬于走到人群中,沒有人能一眼認出她是個大人物的那種類型。
從王志珍的相關資訊來看,在很多場合上著裝都很簡單,不走光鮮路線,而在今天的這個場合,她穿了一身富有氣質的正裝,整個人看上去顯得優雅端莊。王志珍說,自己平時對物質的要求并不高。今天出場,“總要修飾修飾,找一件合適的衣服,那是為了尊重聽眾。”
現在社會很浮躁,很講究外表,天天要花點時間打扮。我們是從來不花這個時間的,因為我們覺得長成什么樣子,跟你做科學研究沒有絲毫關系,主要靠你的腦子。在我們科學院說實在,誰聰明誰做出工作誰最受尊敬。”
快人快語,有問必答,這是王志珍的風格。采訪完后,離開鏡頭,她停留在現場,和身邊的小姑娘們有說有笑地聊起天來,話題不離科研崗位和職場上的女性人群。
中科院我們所里當時只有3個女研究員,現在有20個女教授,而且她們都做得很好。其實在生物學上看,女性和男性沒有任何差別,都是一樣的。我的博士生當中,女性有50%,有的時候會多一點。”
以下是采訪實錄:
談科普教育
網易科技:目前大力倡導科普教育的重要意義在哪里?還有哪些普及辦法需要全社會共同加強、改善?
王志珍:現在大家還是對科普工作非常重視,而且是越來越重視。我覺得尤其需要重視的群體是青少年,因為任何事情就像鄧小平同志講的,都要從娃娃抓起,這是最重要的。提高整個中國社會公眾的這個素質,特別是科學素質,顯然也要從娃娃抓起。
所以我覺得,一些向公眾來進行科學科普的活動是非常必要的。對于小孩子的科學教育,不僅是要平時上課,像我小時候就有很多課外的活動,我曾經養過兔子,種過番茄,像這些事情其實也是很有用的。而不是像現在的孩子那樣,牛奶在哪里,在超級市場,他都不知道這樣的一些事情。
網易科技:像您剛才說的這些現象,其實很多人會認為可能現在學生的課業壓力太重造成的。
王志珍:我們可以看一些其他的科學和技術,所謂的發達國家,他們孩子小時候的生活是非常寬松愉快的,說的極端一點就是在玩的過程當中這樣長大的。而亞洲一些國家的孩子,甚至要拉著手提箱去上課。所以我覺得這就說明,誰輸在起跑線其實也無所謂,還是應該是在愉快中去學習,這是最重要的。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在沒有壓力情況下孩子的成長,身心腦都是更健全的。
網易科技:這個過程中科學家能做一些什么?
王志珍:像我做基礎研究的,實際上是納稅人給的錢,讓我們去做科學研究。 有的人說讓我們去“玩科學”。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有一種社會責任。應該去為公眾服務。所以做科普實際上提高整個社會的科學人的科學素質是我們的社會責任。我作為中國女科技工作者協會的會長,我也在我們女科技工作者協會的工作當中特別重視科普的工作,我們每年都有組織你科技科女科技工作者到基層去到大學去做科普的工作。
談女性科學工作者
網易科技:您剛才演講當中也特別提到女科學家,您是不是特別看重女性從事科學工作這件事?
王志珍:我們科協跟中國科學院曾做過一個調研,就是在大學生跟博士生這個層次,男女的比例大概是1:1。在某一些學科,比如說醫學、生命科學以及外語,甚至于女孩子還會更多一點。但等到教授級,或者到一個大項目的首席科學家,或者到當院士,女性的比例就越來越少,一般就到了10%。
網易科技: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
王志珍:我們也做過一些討論。我覺得主要還是出于這種社會的所謂的傳統意識跟分工。一個家庭,有孩子,有老人,總歸還需要照顧,這些你要分心,所以一般都會是所謂的男主外女主內這樣一個傳統的觀點。還有一種就是近年來,我覺得有一個并不是很好的情況,就是女性會產生一種說我做得好不如嫁得好,這個觀點我覺得是很不健康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女性跟男性在智力方面是完全一樣的,在生物學上講是完全一樣的,最重要是女性還得要自強、自立、自信,你都可以做成很難難的事情。
網易科技:甚至于女性可以做得更好。
王志珍:因為女性更加細致,更加踏實,更耐得住寂寞。在我成長的階段,就是說解放以后,我覺得新中國的男女平等政策執行的是非常好的。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男女平等,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這個女人能頂住半邊天,的確是這樣。
但是大概隨著這個社會的進展和現在的發展。逐漸出現了一些職場當中可能對女性有一定的排斥的現象,我覺得這是不公平。因為人是需要延續的,要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情,要撫養孩子也是女人的事情,當然要整個家庭來支持,但女人承擔的就更多,這就需要每個家庭能夠有很好的合適的安排。只要你安排的好,女性還是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成績來。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女科技工作者做的非常好,就像顏寧。
以前在我那個時代是完全沒有全職太太這件事兒的。 但是現在出現了。所以我說這是社會在進展過程當中出現的這種現象。個人可以有個人的選擇,但是從全社會的進步性來講,男女平等應該是一定要提倡,而且要執行要做的。
談學術嚴謹
網易科技:促使您一直從事科研工作的原因和動力是什么?
王志珍:很多我的前輩是經過抗日戰爭的。那一代年輕人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愿望,就是要愛國,要強國,所以他們覺得我應該去學理科、工科,直接服務于國家,使他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再也不受外面人的欺負。那么像我就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是我覺得新中國這個跟舊中國的對比我還是有的。希望新中國能夠建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我想是我們每個人非常一個基本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是愛國。
第二個,還是跟個人情況有關系,我喜歡理工科。所以這也是個人興趣,喜歡這個工作。別人以為搞科研的沒有假期,但是自己做到那個份上,就喜歡在實驗室里,一直就這么做下去。那時候也沒有特別的物質觀念,說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回報才去做,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情。你看科學家平常都是非常簡樸的生活,對物質的要求也是不高的。尤其女科學家,像我今天是吧,你總要修飾修飾,找一件合適的衣服,那是為了尊重聽眾,平常我們是非常簡單的生活。
網易科技:您之前有個觀點是說,老一輩的科學家物質條件并不是那么的好,但也能夠做出多世界一流的研究。
王志珍:最明顯的就是西南聯大。那是在戰爭年代,現在云南師范大學就是原來西南聯大的舊址,他們就是住在茅草房里的。外面下雨下得很大的時候,老師講課,我們學生都聽不見,物質生活非常艱苦。但是從西南聯大走出的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大批的頂尖科學家。其中有楊振寧、李政道這個就不說了,其實還有一大批從西南聯大出來的科學家,后來都是新中國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主要骨干。
所以說我覺得主要是精神,精神在,在物質極差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做得好)。我覺得是他們的愛國精神,我所有接觸過的老科學家都極其愛國,文化大革命當中受那么多罪,他們在人格上或者在物質上受到很大的摧殘,但是他們沒有什么抱怨,這個國家只要在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仍然毫無保留的把自己貢獻給國家的發展。
第二個是他們治學極其嚴謹,像現在還是出現了一些急功近利,吹噓夸大,甚至于造假的現象,我覺得在我認識的老一輩科學精神我都沒有看到。 10分的事情,他們可以只說8分9分,他們決不會說到11分12分。這是最起碼的道德跟品質。
我認為現在還是需要宣傳教育,還是應該要把重心工作放在人的責任心、誠信等基本道德建設上來。
談基礎科研
網易科技:您演講時特別講到基礎研究的問題,您覺得提升科研原創力,關鍵應該做一些什么?有哪些問題值 得注意?
王志珍:國家現在對于基礎的研究,很多人認為投入還不太夠。我自己因為是跟以前有比較,還是覺得國家的投入一直在增加,我并不抱怨,說投入不夠,因為我看到周圍的人并沒有說都沒錢不能做了。這個事情我覺得很少,除非是大型科研裝置的投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看到周圍,特別是最近一大批從國外回來的人,他們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支持。所以國家是重視。當然在國家發展過程當中,可以對技術研究有更多的投入。
基礎研究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一個國家的源泉。成果的儲備跟人才的儲備是要靠基礎研究的。沒有這些儲備的話,那么你要有轉化成果,要做出產品來,就會面臨現在大家說的“卡脖子”的情況。
不想被卡脖子,都是要靠你的技術知識儲備、科研儲備跟人才儲備。是不是經費越多,它可能就越能解決問題越能出成果?可以這么簡單理解嗎?我覺得不是。現階段我們國家雖然已經發展得非常快了,也被人家說成中國人現在有錢,我認為還不是那么回事,我們還是要非常清醒地看到,我們并不是那么有錢。因為中國有14億人,什么事情都以14億人來除一下的話,你就不是老二了,不是第二位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有限的錢用到刀刃上。怎么花錢,怎么用到刀刃上,這才是主要問題。
談“唯論文”論
網易科技:現在這個時代,年輕人的偶像偏向娛樂化,您怎樣看待這樣的事情?
王志珍:你要我回答一句話好或不好,我就說不好。但是社會發展以后,它的文化就是多元化,這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但我認為還是需要宣傳部門把教育的重心放在人的責任心、誠信、基本道德和守法上。我們國家要成為一個法治國家,這個也要從娃娃抓起。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過度娛樂化,我是很不喜歡的。看一些搞笑的東西覺得很開心,但我覺得這對青少年發展沒有什么好處,大家不如好好的去念一點好的書。我覺得宣傳部門必須要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網易科技:您怎樣看待“終身學習”這四個字? 您現在也有80歲了,似乎仍未脫離科研崗位。
王志珍:終身學習是必須的,也必然的。說實在的大學里那點東西都是基本的科學知識,你要將來做科學研究也好,教書也好,或者你到公司里去做事情也好,你未來的職業生涯仍需要大量的知識跟能力。所以每個人在工作的過程當中,都在學習你工作所需要的知識能力,所以是必須要從終身學習。
網易科技:目前有一種觀點是“唯論文”評價已經嚴重阻礙中國科技發展,您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的?
王志珍:科學研究成果的體現,很多情況下要用論文來體現。博士生最后他要有一個博士論文,他要答辯通過,在這期間他要做很多的科學研究,他要發表科學文章,這個是必須的,這是一個做基礎研究人才必須具備的一個素質,他還要會表達他的研究成果,這就是論文。
但不能“唯論文”來評價一個人和一項科研成果。科技界的人要能夠有對科學的鑒賞力,這個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確對科學本身有鑒賞力的話,你就知道這個人做的工作重要性是什么?比如說甲做了4、5篇文章,乙才做了一篇文章,您說這個甲的成果一定就比億多5倍,絕對不能這么說。你要看乙那一篇文章它解決的問題,他提出的問題跟解決的問題是不是更大的,它是不是是一種顛覆性的、一種創新的東西。有的時候需要同行評議,叫科技界的這些人來評價它的研究成果價值,這個最重要。
王志珍簡介:
中國科學院院士,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1942年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1964年畢業,同年9月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5年當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她獲得了新中國第一批德國洪堡獎學金,1981年獲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Fogarty獎學金分別在德國和美國做訪問研究,后在德國和香港任訪問教授。1993年在蛋白質折疊的前沿領域建立了"幫助蛋白質折疊的生物大分子"的研究,開創了國內折疊酶和分子伴侶研究的新方向。